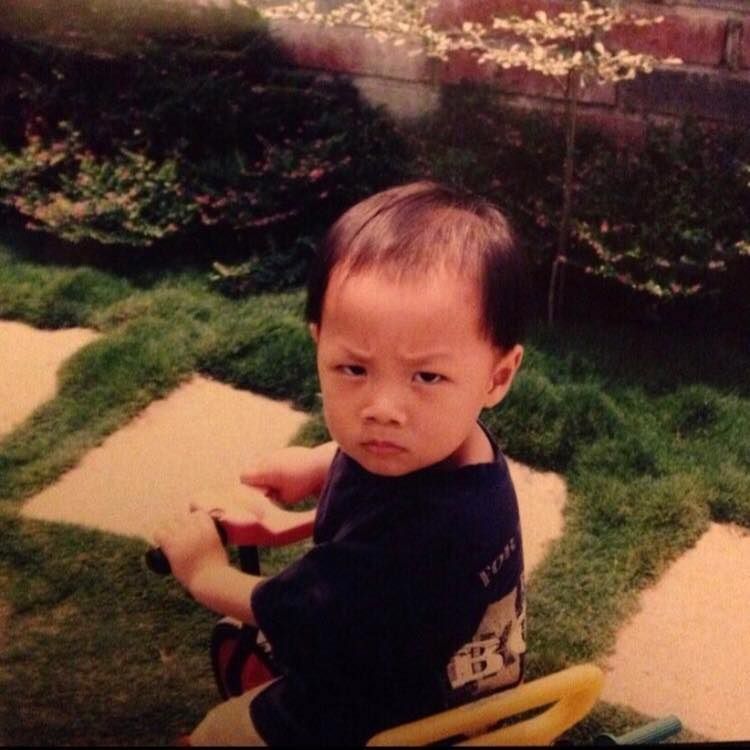
https://liker.land/hong5ui7sh09/civic 單純說說心裡話 路過加減看 想留下或說說話 我們泡泡茶
兩篇以前寫的稿子,上下篇乾脆合在一起
射到W的耳中,擊打著他的腦袋。
他放下手機,反正這副疲倦卻又不肯好好睡一覺的軀殼沒有要原諒W的意思,乾脆聽一聽外面在幹嘛。
「為什麼要逼我?」
雖然外面的人是竭力嘶吼,但是有許多斷句、字詞是聽不懂的。他們完全無視十點過後不能製造噪音的規定,鬼哭神嚎。
「對,我就是自私,我就是沒在考慮你!」
接著出現一串物體碰撞後倒地的聲音,還有掉到柏油路上的那種不太清脆卻感受得到物體結構受到損傷的悶響。他們開始搬動一些東西,推倒一些東西,奔跑,急停,丟擲,拿起一些東西用力敲打。敲打著車窗,敲打著機車座墊,敲打著路燈,敲打著樹幹。
「出來,給我出來!」
他們開始挨家挨戶敲打門鎖和鐵門。門的防盜機制太過安全的話,他們直接把鐵窗打爛,然後闖進其他人的家裡,製造出爭執、恐慌的那種尖叫,隨後安靜片刻,便傳來把東西丟進大水溝的那種落水聲跟漣漪的延續。
緊接著是下一門戶。
沒有人被吵醒。
這時輪到W的家門。他不敢回應,打算拿起手機報警卻找不到該死的手機。敲打著鐵門的迴響一次、一次的導入W的房間,震動著玻璃、窗戶、牆壁和床,但是他們沒有闖進來,但W的床也被這樣的迴響搖晃著。急促的腳步踏在介於一樓和二樓的鐵皮上,他們沿路打爛了看到的鐵窗,白鐵扭曲變形,碎裂不堪,他們卻沒有直接進來W的房子,而是繼續尋找其他可以敲打的東西,不斷地打、不斷地敲、不斷地製造那種迴響。腦神經也許錯位了,W眼前一黑,放聲大叫,瘋狂地捶著牆壁,深藍色的牆壁卻無動於衷。幾次之後,W的手已經毫無感覺,然後,他換用額頭,再一次這樣的循環。
眼前慢慢浮現牆壁的景象。他涼涼的。那些迴響也不再,在鐵皮上的腳步緩緩地離去。W又倒在床上,他感到非常疲倦,閉上雙眼,上半身的疼痛襲來。他想洗把臉,洗去淚水,好好睡一覺。
甫起身,兩個人在W的面前,W還來不及反應,就感受到脖子上溫熱的手掌和被揪起的頭髮,接著眼睜睜看著深藍色牆壁上的痕跡,便一頭撞上。在昏沈當中,他的吉他、他的書桌,他的電腦,他的印表機⋯⋯那兩個人將這些東西砸在那片深藍色牆壁上,把所有的玻璃、鐵框、窗戶都破壞無遺。直到失去意識之前,W的房間裡都還是那兩個人敲打著所有物體的,在W腦袋裡震動著的那些聲波。
後記
我看到幾個人在我的房間徘徊,沒有說話。他們到底長什麼樣子我說不上來,可是他們黑黑的,安安靜靜的,看著我。其中一個拿著刀子刺向自己,另一個一顆一顆地將藥丸吞下肚,還有一個的脖子鎖著一條繩索,還有一個已經倒在地上。可是他們都看著我。我正在抵抗加入他們。或許是因為將力氣都用在抵抗他們,所以我這幾個月都非常的疲倦,不想說話,步履蹣跚。他們沒有對我提出邀約,可是,維持意志力與意識非常痛苦,非常疲倦。
請提醒我每天都要上臉書罵幾聲幹,跟大家要錢。如果兩三天都沒有,請幹這個世界。不管我活著還是死了,你都還有機會帶包菸給我。
------------------------------------------------------------------
「爸,我把水果放這裡喔,記得吃。」
W看著這張貼在水果盒上的紙條,摸了摸頭。也是,這個時間該是午休時間結束,回去上班的時候了。住在這樣的病房,一切都好,但是終究是有人養的啊,大家如果任何時候都在這裡,好像也很矛盾。
W按下床邊的紅色按鈕。不多時,護理師快步走來,看到W坐在床沿,擠出一絲微笑問說,怎麼了。
W搖搖頭,就看著他。
「你要找C嗎?他還在忙。我可以幫你說,但是你再等他一下下,好嗎?」
W看著他。
在一片安寧當中,W坐在床沿,沒有特別的表情。接著他轉頭看看窗外的晴朗天氣,幾隻鳥停在外頭的木椅上,跳了跳,跳了跳,然後振翅離開。花草樹木都隨風搖擺,做他們的日光浴。
下一隻鳥在哪?W不知道,他餓了,卻不想吃東西,坐在床沿的這幾個小時其實挺無聊的,孩子應該是還沒下班,不然通常,他們都會來的。聽說,女兒接了不少案子,每天都要加班;兒子在打拼他的博士論文跟結婚的事情,偶爾才出現。擺在床頭的老婆的照片就像是新的一樣,未曾動過。
帶著半包長壽菸,W走到庭院,挑了一個最偏僻、最邊陲的燈光下,劃了一根火柴,滋滋地抽起菸來。
連最後一段日子都是這麼疲倦⋯⋯原本以為,能開心地走完呢。
W回頭看,可是沒有人在那裡。他聽到腳步聲,踩著草地而來。可能是其他出來抽菸的人吧,不過,如果是這樣,應該會有一些火光,但沒有。
「誰啊?」W問。
「我。」
「誰?」
「我。」
那道踩過草地的沙沙的聲音是非常鮮明的,燈光也沒有照出什麼影子。可是W的肩膀被拍了幾下,好似有一個「人」繞過了他坐的木椅,在旁邊烙腳。
「你不怕我嗎?每次我這樣,大家都以為我來帶他們走的。」
「要帶就帶啊,爛命一條。這句話我從年輕說到現在,沒在扯的。」
「⋯⋯別急嘛,你心裡在想什麼我看的一清二楚。時候還沒到。」
「到你媽,早點走不好嗎?每次有人死了我都覺得更不爽,不是因為他們先,而是他們又把病房讓給另一群爛人。」
「⋯⋯」
「抽煙嗎?」
「你抽就好。我都吸其他的。」
滋茲,W又劃了一根火柴。
「我」亮出自己的獠牙,開始啃食W的右手,接著是右肩膀,接著是脖子。一排牙齒刺入W的皮膚,讓他血流如柱,隨後「我」用繩索把W的雙腳綁著,緊得近乎砍進腳踝。
「留我的手跟嘴,我要抽煙。」
「我什麼都沒幹啊。」
W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完好如初。
「真的是屢試不爽。那些年輕小伙子一遇到我就頭皮發麻、四肢顫抖,好像我是個殺人魔一樣。可是像你這樣的人卻好像抽煙比命還重要,心無旁騖幹著這件事情,哪天遇到真的殺人魔也會很平淡。」
「我想了半天,你到底是誰?」
「我。」
霎時「我」將一把白刃劃開W的額頭和鼻樑,雪亮的骨頭見了月光。隨後白刃被收進胃袋做的刀鞘,「我」徒手扒開W的皮,撕裂著W的肌肉。但是W無動於衷。「我」玩起了W的神經,搞得四肢亂顫的W開始有點煩躁。
「你知道『I am in pain』是什麼意思嗎?」
「我」問道。
「這是懸在我心頭上一輩子的問題。可是我現在不知道。你也懂維根斯坦?」
「我找過他滿多次,他的反應跟你差不多。差別是他心頭上是幾個男人,但你心頭上很空洞,真的要講就只有尼古丁。」
「你打多少麻藥給我?」
「不知道。」
「我」若無其事回到W的比肩。矇住W的眼睛,將它倒吊在旁邊的樹上,並朝W的鼻腔灌水。
「咳咳⋯⋯咳咳咳咳咳⋯⋯」
「哈哈哈哈哈哈北七,幾歲了抽煙還會嗆到,虧你抽黃長壽,跟會抽寶亨一號的臭小鬼一個樣。」
「幹你娘。」
「我」向W釋出了一些善意,表現在W回過神來看見這根菸才甫點燃上。
「你害怕我嗎?」
「還好,沒什麼感覺。」
「我」在W面前勒死了W的孩子。用W的火柴熊熊燒掉這幾具屍體。那股硫磺的味道混雜了長壽的茶香味。
W看了看。
「你是誰?」
「你認識我啊。」
「你到底是誰?」
「我。」
W感到一陣反胃,橫隔膜激烈的劇痛。
他沿著破曉的微弱光線,走回病房。這樣的疼痛讓他打翻了許多東西,最後他把那盒水果掃到地上,在一片雜亂當中找到了止痛藥。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