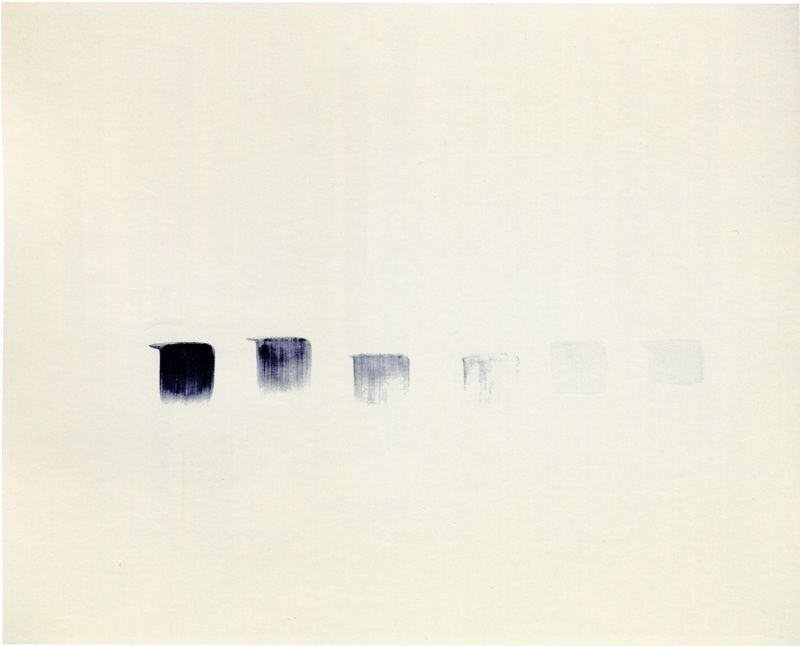
在寫字的路上走呀走(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protected]
說書人重回劇場《一桿稱仔》
戲劇 2015–11–26 影響.新劇場

演出 影響.新劇場
時間 2015/11/20 19:30
地點 台南人戲花園
文 — — 羅倩
「影響‧新劇場結合環境,以極簡主義式的肢體劇場,透過三位演員的肢體、吟唱與敘述,用臺語、白話文、日語多語混雜,凸顯小說創作時代裡的語言困境與被壓迫者的無所適從,將小說化為立體閱聽劇場寓言。」[1]
劇場的表演形式如何演繹經典文學作品?影響‧新劇場的《一桿稱仔》因應2015臺南文學季「城市X文學X劇場」將三年前的舊作重演。導演呂毅新提到她的處理策略是「向文學致敬,而不改編」,如何在尊重文學原著的情況下向台灣現代文學之父賴和致敬?導演的改編策略為何?如何應用到劇團強調的「環境劇場」風格,同時論及表現形式、肢體與多語敘述策略,本篇評論將依這幾個問題來作討論。
由戲劇學者理查‧謝喜納(Richard Schechner)所建構的環境劇場(Environmental Theater),在1968年〈環境劇場的六大公設〉提出了六點界定[2],以此界定來討論影響‧新劇場的「環境劇場」,從最初的界定可以了解到,以此齣戲來說,觀眾和演員的距離是相當親近的,只有一線之隔,整個321巷藝術聚落台南人戲花園老屋的前院及周遭,都是演員表演的活動區域,觀眾也包含在表演場地之內。演員可以從屋外門前走進,也可以隨著演出移動到觀眾視線幾乎看不到的左右兩側。唯一和界定不同的是,試圖忠於原著小說《一桿稱仔》(1926)的改編嘗試。
在形式的極簡主義下,沒有多餘的道具,三位演員、三支長竹竿、三副模糊個性的塗白抹紅臉孔、三套黑白灰層次的植物手染上衣、編織垂飾與頭巾,用話語傳達敘事、肢體表達情緒、以及透過長竿的敲、擊、甩、碰等多變化使用,製造聲響。甚至音效也使用的相當俐落,不過度渲染人物情緒,偏好帶入一種靜謐的情境,因此連秦得參最後的反撲弒警與自我了結的終場,也僅透過演員的話語表述,任由觀眾在心中想像最後的情景,淡化了劇情結尾的張力。
回到原著與改編的策略,賴和使用不算熟練的白話文寫作,從文學作品到話語劇場,勢必有其改編的調整,以符合表演重話語的策略。三位演員角色任意轉換,因此在演出中,秦得參和妻子以及劇情旁白解說講的是台語與國語,偶夾雜解釋台語的國語解說。日本警官則置換成日語與台語解說。單就戲劇的語言策略來說,對於解釋台語與日語甚或是對於劇情的旁白提示,是否有讓觀眾脫離劇情之感,而產生觀看與聽覺的不協調。這也許是改編賴和白話文中也有台語的思維在文字裡的複雜度有關,再轉換成表演時的權宜之計。但由於小說並沒有出現日文,導演改編時讓日本警察講日語,是否有太過於用口語二分兩個台日對立,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將背後歷史因素造成的複雜的語言關係簡單化了,實則為力求忠於原著下又必須處理表演與戲劇呈現的兩難。
另一方面,或許可以說,戲劇《一桿稱仔》透過演員飾演說書人的角色,讓文字重回口語,讓說書人重回當代,如同本雅明(Water Benjamin,1892–1940)〈講故事的人〉一文所言:「使一個故事能深刻嵌入記憶的,莫過於拒斥心理分析的簡潔凝練…聽故事時,人們不再羅織細節,增奇附艷。聽者越是忘懷於自己,故事內容就能深深地在記憶上打下印記。」[3]賴和的經典文學作品飛離文字,跳躍上劇場舞台,透過意象性的肢體演出與多語言的敘述與旁白策略,深化了故事對於觀眾的視聽經驗,故事主角秦得參再一次內化成我們的民族與歷史記憶,以便用記憶與感知重新召喚其現身。
註釋
1、引用自2015臺南文學季「城市X文學X劇場」手冊中文宣。
2、六個界定為:1. 劇場活動是演員、觀眾和其他劇場元素之間的直接面對、交流。2. 所有的空間都是表演區域,同時,所有的空間也可以作為觀賞的區域。3. 劇場活動可以在現成的場地或特別設計過的場地舉行。4. 劇場活動的焦點多元且多變化。5. 所有劇場元素可以自說自話,不必為了突出演員的表演而壓抑其他劇場因素。6. 角本可有可無。文字寫成的劇本不必是一個劇場活動的出發點或終點。鍾明德,《從貧窮劇場到藝乘:薪傳葛羅托斯基》,台北:書林,2007,P194–195。
3、本雅明著,漢娜.阿倫特編,張旭東、王斑譯,《啟迪:本雅明文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P102。
2015–11–26首發於表演藝術評論台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